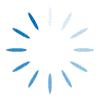皇帝足足愣着很久:“什么时候?”
“昨天夜里。”
皇帝闭上眼,胸膛不住地起伏。昨天夜里,她素来无灾无病,怎么会走的这样蹊跷,究竟是什么人,竟然连让他们见最后一面都容不得?
皇帝离宫的时候确实对小齐后有些不满,可是她毕竟是自己纵容了十多年的小妻子,他即便怨她,冷落她,也从没想过,有朝一日,小齐后会比他还走得早。
皇帝停顿了很久,才问出这句话:“她在哪里?”
皇帝站在坤宁宫,终于再一次见到小齐后,然而这一次已经隔着生死。淑妃站在皇帝身后,她不动声色地瞅了眼皇帝的神情,举起帕子拭了拭眼角,低声道:“陛下,您刚刚回来,要节哀顺变,保重龙体啊!皇后她若在天有灵,想必也不愿意看到皇上为了这件事伤害龙体。”
说完之后,淑妃若有若无地喟叹:“皇后她比我还小许多,我怎么也没想到,竟然是皇后这个年轻人先走。”
这一句话不知戳到了那里,皇帝出奇地愤怒起来:“她死于毒,她竟然是被人用毒杀死的!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是谁,竟然这样大胆!”
显然皇帝也不觉得皇后是自己服毒的,种种迹象都表明,这是谋杀。
淑妃露出难为情的神色,却偏偏摇头不说。皇帝一看淑妃的神色,就知道这件事有异。他沉着脸问:“说,到底是谁!”
淑妃叹了口气,她身后一个宫女怯怯地说:“娘娘赶来的时候,皇后娘娘已经气绝了。当时坤宁宫里并无外人,不过……”
宫女悄悄瞅了眼后面的楚锦瑶,低声说:“不过,太子妃身边的嬷嬷在坤宁宫里,已经畏罪自杀了。”
楚锦瑶平视前方,眼睛都没朝别的方向转,玲珑微微出来一步,本着脸骂道:“放肆,如今并无证据,谁给你的胆子,竟敢不敬鬼神,污蔑死者,称洪嬷嬷为畏罪自杀?”
宫女被训得脖子一缩,低头不敢再言。淑妃瞅了眼皇帝的脸色,眼中微微露出笑意,转瞬又变成悲痛和愤怒:“简直无法无天,在陛下面前,谁准你一个奴婢说话?”
“淑妃娘娘这话真是偏颇。”楚锦瑶接过话,说,“本便是你的宫女没有允许便自作主张回话,她信口雌黄时你不呵斥,反倒是玲珑纠正,你来呵斥无礼了?”
“信口雌黄?”淑妃冷笑,“那太子妃说说,我这个宫女哪里说的不对?深更半夜,你的贴身嬷嬷为什么会出现在皇后的宫里?昨日皇后被人毒杀,这个老奴恰巧出现在坤宁宫,依本宫看,多半就是她毒死了皇后,之后怕皇上回来治罪,便畏罪自杀。”
“若是畏罪自杀,她大可以服毒,痛痛快快死去,为什么非要撞柱?”楚锦瑶紧紧盯着淑妃,回道,“淑妃大概没接触过多少史书,触柱而亡,一概都是被逼无奈,为了表示气节而壮烈为之。淑妃大可以去翻史书,或者找大理寺的卷宗过来看看,看看真正畏罪自杀之人,都是怎么死的。”
淑妃被反驳得卡壳了一下,楚锦瑶确实说准了当时的情形,一般畏罪自裁之人为了速决,并不会给自己找太难受的死法,撞柱子更是不可能。淑妃短暂地停顿了一下,迅速转变说辞:“畏罪自杀之人本就不能以常理推之,她是为了逃脱陛下的制裁,至于是怎么死的,这不过是个人的选择罢了。相反,她出现在坤宁宫,而且和皇后之死脱不开干系,这却是板上钉钉的铁证。”
“出现在坤宁宫,大可是被人掳来的,若只是因为出现在坤宁宫便有嫌疑,那淑妃为什么不怀疑皇后身边的几个宫女内使?依我看,他们积年累月跟在皇后身边,皇后的衣食住行都经他们之手,他们给皇后下毒,应当更容易才是。洪嬷嬷一个外人,便是她给皇后端来有毒之物,皇后警惕之心这么重,怎么会入口呢?”
“皇后娘娘以德化人,她身边的人怎么可能背叛她?”淑妃说道,“太子妃为了给身边人脱罪,也不能诋诬皇后的德行和名誉啊。”
这话也亏淑妃能说得出口,小齐后以德服人?楚锦瑶不屑一顾,可是偏偏,皇帝愿意相信。人一旦死了,那所有的缺点和错误都化为乌有,生前的好反而无限放大。
秋霜一直在殿外竖着耳朵听着,听到这里,她用力揉红眼睛,飞扑着跪进殿内,哭道:“太子妃,您说什么都可以,但唯独不能抹灭奴婢对娘娘忠心啊!蓝玉姑姑为了娘娘,已经被凶手一同杀害,奴婢只恨当时没有长出三头六臂,不能拦住那个凶徒,救回娘娘。陛下,娘娘生前一直盼着您回来,直到临死时还吩咐奴婢梳头,她那样期盼您,您可千万要给娘娘做主啊!”
皇帝声音喑哑,问:“你看到了,动手之人是外面那个老奴?”
“奴婢没有看到直接过程,但是奴婢打水回来,正好看到洪嬷嬷从正殿里出来。”
皇帝露出气愤之色,玲珑几人慌了,连忙看向楚锦瑶,指望着楚锦瑶挽回劣势。然而楚锦瑶并没有看皇帝,而是转过身看向秋霜:“你将昨日你遇到洪嬷嬷的情况详细说一遍。”
秋霜露出戒备的神色,小心斟酌地说:“娘娘当时嘱咐要梳妆,奴婢便出去打水净手,谁知回来时正好撞见洪嬷嬷,她行色匆匆,低着头往外走,奴婢心存疑虑,就赶紧进去看娘娘,结果却看到……奴婢又惊又怒,立刻就跑出去叫住洪嬷嬷,洪嬷嬷看到奴婢非常吃惊,她想哄骗奴婢靠近,好用毒害死奴,奴婢自然不肯,就赶紧喊外面的人,洪嬷嬷见事情败露,便狗急跳墙,直接撞柱子自裁了。她临死前还说,这下死无对证,便什么也查不出来了。”
死无对证,确实是死无对证。小齐后,蓝玉,洪嬷嬷,每一个人都死的不甘心。
楚锦瑶心中动气,但是头脑还很是冷静。淑妃眼底满是得意和示威,楚锦瑶看在眼里,心底却越来越清明,她缓缓说道:“你在说谎。”
这四个字掷地有声,把众人都镇住了。楚锦瑶让人取来东西,而自己继续说道:“如果真如你说的,你并没有被洪嬷嬷近身,那你的扣子,怎么会在她身上?”
淑妃一看到纽扣脸色大变,秋霜也才想起来,昨日她哄骗洪嬷嬷出去时,洪嬷嬷确实狠狠撞了她一下,没想到趁这个时间,她还拽了个扣子下来,藏在身上。
秋霜眼珠子乱瞟,慌忙说:“奴婢记错了,洪嬷嬷看到奴就跑过来捉人,奴婢和她纠缠了一会才脱身,这个纽扣就是这段时间被她拽下去的。昨天奴婢实在是太惊慌了,一时记错了……”
楚锦瑶冷哼一声,转身去看皇帝:“皇上,这个奴婢颠三倒四,证词前后模糊,如果她真的经历过,这么重要的细节,她怎么会记错?这只能证明她在说谎,她的证词不可信。”
淑妃立刻反唇相讥:“怎么不可信,因为她指认太子妃身边的人,太子妃便说她的证词不可信吗?”
“淑妃一开口就这样笃定,恐怕是知道什么,才敢这样肆意攻讦吧。”
“都够了!”皇帝大喝一声,说,“她都已经走了,你们还是不肯让她消停。都出去吧,这事朕自有决断。”
作者有话要说:【小齐后下线】
之前小齐后出场的时候说过,她是宫斗部分小boss,因为大boss是淑妃啊。
第129章 父子猜忌
楚锦瑶从坤宁宫出来,一路不说也不笑,直接往慈庆宫走去。玲珑几人也没了说笑的心思,直到走进慈庆宫,玲珑才敢将疑问问出口:“太子妃,皇后这事……皇上会怎么处理?”
这谁知道呢,皇帝说他自有决断,可是清官不断自家事,就是因为再清明的人都会被情绪蒙蔽,而皇帝还不是个清楚明白的人。
玲珑和丁香也意识到这个势头对他们大为不利,丁香忍不住说:“太子妃已经把证据都摆出来了,那个秋霜的话明明疑点重重,皇上为什么不信太子妃?”
“他不是不信我,他是不信权力。”楚锦瑶说着进了门,抬头一看,顿时怔住,“殿下,你怎么回来了?”
秦沂正在东次间看书,听到动静,他放下书朝外走来。仿佛是往日的情形颠倒,楚锦瑶数不清多少次到门口迎接秦沂,却很少有秦沂比她先回来的时候。
看到太子,玲珑几个丫鬟麻利地给楚锦瑶卸下外面的重衣裳,然后就低着头退下。楚锦瑶随着秦沂坐到东次间,秦沂问:“听小林子说你去坤宁宫了。怎么样?”
楚锦瑶摇头,秦沂对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,他随意一笑,安慰楚锦瑶:“别太在意了,你尽力就好。”
楚锦瑶如何不知道尽人事听天命的道理,可是大道理之所以为大道理,就是因为人人都会说,却未必有几个人能做到。
楚锦瑶接触到他平静无澜的眼神,心里不知为何感到不痛快。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有一副铁打的心肠,秦沂变成如今这种薄情冷静的模样,恐怕皇帝居功甚伟。
楚锦瑶说话的语气不由温软下来:“殿下,既然你回来了,为什么不去坤宁宫看?”
“我去了,情况只会更糟。”秦沂说这句话时非常冷静,早在他下令拒绝瓦剌议和的时候,或者更早,在他监国的时候,他就已经预料到这一天。
自古君王皆薄幸,最是无情帝王家。每朝每代的太子都逃不掉被猜忌的下场,他也一样。淑妃的局中有许多破绽,可是正如楚锦瑶所说,一个人只会看到自己想看的,不然,即便楚锦瑶和秦沂将这些摆带皇帝眼皮底下,他也会视而不见。
到现在,已经不是小齐后之死的问题了,这是皇帝更愿意相信秦沂还是肃王的问题。
秦沂不甚在意,他反而非常小心地看着楚锦瑶的肚子:“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,虽然四个月到八个月比较稳,但是也不能操劳太过。他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,你只管安心养胎,不用管他们。”
楚锦瑶也觉得烦,她只是有些遗憾,放宫女出宫这件事,看来只能暂时放下了。楚锦瑶正打算和秦沂说什么,突然神情一怔,随即就惊喜地对秦沂说:“快来,他又动了!”
秦沂也精神一整,自从进入正月,胎动越来越明显,秦沂早就听楚锦瑶说过孩子会踢她,但是因为政事忙,一直无缘得见,直到正月诸事落定,胎动也日益频繁,秦沂才亲手摸到胎动。
秦沂第一次触碰到胎动时深感奇妙,到现在,他再一次将手放在楚锦瑶的肚子上,依然觉得不可思议,这里面便有一个融合了他和楚锦瑶血脉的孩子,再有三个月,他就能出来了。
这个孩子似乎感觉到父母情绪不高,现在正努力彰显自己的存在感。楚锦瑶轻轻笑了起来:“你也听到了是不是?又在怪罪我们疏忽了你。等你出来的时候,京城正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,到时候娘亲带你去看桃花,你一定喜欢。”
秦沂不知不觉也放柔了神色,是啊,等春天的时候,他最珍贵的礼物,就要降临了。
.
乾清宫里,皇帝对着金雕玉砌的宫殿,头一次觉得这帝寝空荡荡的。
明明只过去几个月,而皇帝却深刻地觉得自己苍老下来。
这种感觉在他看到前来奏事的六部尚书时,越发明显。
如今的六部骨架都是战时由秦沂提拔起来的,整个朝堂说是大换血也不为过。皇帝熟悉的面孔,竟然一个也看不到了。
若皇帝肯再往深想一想,就能想到,他熟悉的面孔之所以再也看不到,是因为这些高官都死在宣府事变。
可是皇帝只是感慨,并不深思,他叫来礼部的官员,说出自己的想法:“皇后她陪了朕十五年,还替朕生下一儿一女,她比朕小了那么多,却早早的就走了。朕没能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,只能在后事上加倍补偿她。皇后的丧仪,要好生操办。”
礼部尚书和自己的副手侍郎对视一眼,都露出为难之色。礼部尚书上前一步,拱手问:“陛下,您说的大办,是指比照什么规格?”
皇帝简直觉得这个问题莫名其妙:“至少不能比文孝的差。她们俩是同胞姐妹,没什么先后之分,比照文孝当初的规格就是了。”
礼部尚书越发为难,先不说小齐后作为继后,丧礼规格和长姐兼元后齐平合不合礼法,就只说建兴八年和现在的国力情况,就不能同日而语啊。
建兴八年,天下承平,国库丰盈,文孝皇后作为皇长子的母亲,后事风光大办没有任何问题,可是现在呢?小齐后犯了众臣的忌讳,间接害死许多人,整个国都差点撑不过来。如今百废待兴,京城刚刚重建完,正是需要修生养息的时候,却将国库大部分的钱花在给小齐后办葬礼上?
别说内阁和户部能不能同意,便是礼部尚书这个主管祭祀国典的专职礼官,都不会愿意这种事。
礼部尚书沉默,无声地表态。皇帝看到这里,十分惊讶。他是堂堂天子,现在只是想让陪伴了自己多年,如今还死的不明不白的妻子有一场体面的葬礼,这都不行吗?
皇帝的脸也拉了下来。
好在僵持了没多久,太监禀报肃王来了。礼部尚书借机告退,出门时,礼部尚书看到肃王,站住身对肃王行礼:“肃王殿下。”
“尚书不必多礼。”
皇帝还在里面,这不是一个寒暄的场合,两方人短暂地问候过后,就彼此别过。错身而过时,礼部尚书看到一个穿着青衫的单薄儒士,他的模样和进京赶考的书生别无二致,可是能出现在这种地方,便注定他不会是一个普通书生。
礼部尚书并没有在这个人身上投注多少注意,这个时候,他还只是把这个青衫书生当成一个普通的近臣罢了,天子也是人嘛,总是有偏好和亲疏的。
肃王和方濮存走到内殿,躬身行礼:“参见皇上。”
皇帝终于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,他亲切地对方濮存说:“你在京城,住的还习惯吗?”
皇帝从瓦剌回来,自然把大功臣方濮存也带出来了。皇帝牢牢记得那段时间,议和使臣故意拖延时间,瓦剌人的态度越来越恶劣,是方濮存左右周旋,一力把他救出来的。现在看到方濮存,皇帝心里说不出的亲切。
“禀陛下,臣一切都好。”
肃王关切地问:“父皇,您在瓦剌受寒,回来后可召太医看过了?”
平安脉当然早就请过了,皇帝身体没什么大碍,但是因为这一冬天担惊受怕,以及塞外的寒冬不比宫中处处烧着地龙,所以皇帝不免损耗身体,底子有些虚。皇帝这几日天天喝药,听到肃王的问候,皇帝心头涌上热流,眼神也变得和蔼起来:“太医来过了,说来说去就是那一套。反倒是你,一直记挂着朕的身体,有心了。”
肃王不远千里亲自护送皇帝回京,皇帝如今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。秦沂是太子,天然吸引着众多目光,走到哪里都光芒万丈,而三皇子是小齐后的儿子,有小齐后帮衬,皇帝也偏疼幼子几分,所以身为二儿子的肃王是最受疏忽的。皇帝也是现在才发现,原来二儿子长得英武挺拔,仪表堂堂,尤其难得的是,极为纯孝。
肃王低着头谦辞:“父皇谬赞了,儿臣无甚才能,胸无大志,所求不过是安稳度过这一生罢了。为父亲尽孝是儿臣的本分,儿臣不过关心父亲的身体,做些琐碎的小事,论起孝心,怎么能比得上为父亲分忧的皇兄呢。”
皇帝脸色不觉冷下来,他想起来,自他回来,秦沂似乎还没主动来请过安。上次秦沂是随着一大帮臣子,敷衍又官方地问了问,便继续去文华殿处理政务了。而且,皇帝慢慢发现一件事,秦沂不肯叫小齐后为母亲,其实也没叫过他父亲。无论公开还是私下,秦沂总是叫他“陛下”。
肃王仿佛没有察觉到皇帝的脸色,依然一脸恭谦地站着。方濮存看了看,说:“陛下,你如今身体欠佳,正是需要子女侍疾的时候,但是太子忙于政事,恐怕抽不出多少时间。”
肃王立刻上前一步,行礼道:“儿臣愿意侍奉父皇,为父皇分忧。”
皇帝想了想,说:“你毕竟已经有家室了,长时间把王妃留在庆阳也不成样子。这样吧,等过几天天气转暖,让肃王妃也一同过来吧。”
肃王大喜,躬身行礼道:“谢父皇。”
皇帝继续和方濮存说话,肃王等了一会,借机告辞。离开前,方濮存和肃王的眼神飞快地对上,又状若无事地移开。
成年的皇子不得留在京城,肃王身为男子,无论是会封地还是回京城都方便的多,但如果皇帝让肃王妃也搬回京城,那意味就不一样了。
女眷也在,至少说明皇帝有意让肃王长留京城,一时半会,是不用走的。
父子猜忌,竟然已经到了不需要掩饰的地步。
第130章 后来居上
肃王妃不日即将赴京,这下全京城人都知道了,皇帝对太子似有不满,故召素有贤名的肃王留京。
皇子成年后,除非被立为太子,否则不能留在京师,而肃王夫妻却特意被召回京城,皇家这片不见硝烟的战场,慢慢展露出骇人的刀光血影来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